腊月的风跟刀子似的,刮在老五脸上生疼。他裹了裹身上那件打了七八块补丁的单褂子,布料薄得像层纸,根本挡不住寒气。脚下的布鞋早就磨穿了后脚跟,露出的脚后跟冻得通红,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碎石子硌着肉,可老五像是没知觉似的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集市那头飘着的酒幌子。
1957年的冬天特别冷,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,家里的粮缸底朝天,连掺了糠的窝窝头都得省着吃。老五家更是穷得叮当响,老婆孩子整天饿得有气无力,只有老五,只要一想到集市上的土酒,就浑身是劲。
集市上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,大多是攥着皱巴巴的毛票,在摊位前犹豫半天才能买下点东西。卖土酒的摊子有三个,都支着大陶缸,缸口用红布盖着,旁边摆着几个粗瓷小碗。老五先凑到最东边的摊子前,摊主是个络腮胡大汉,正给一个老头打酒。老五清了清嗓子,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正经买主:“掌柜的,你这酒醇不醇?我想买点过年。”络腮胡抬头看了他一眼,见他穿得破破烂烂,态度冷淡但又不想失去生意,敷衍地说:“你尝尝不就知道了。”说着就倒了小半碗递过去。老五接过碗,仰起脖子一饮而尽,辣辣的酒液滑过喉咙,暖意在肚子里散开,他舒服地眯起眼睛,砸了砸嘴:“嗯,是不错,就是有点冲。我再去别家看看,对比对比。”说完,不等络腮胡说话,就颠颠地走了,换到了下一家卖酒摊子前。
这摊子的摊主是个老太太,老五同样装出要买酒的样子:“大娘,你这酒咋样?”老太太心善,没多想就给了他半碗。老五又是一口闷,抹了抹嘴说:“大娘,你这酒挺绵柔,就是度数有点低,我再看看。” 说完又溜到了最西边的摊子。
一来二去,老五在三个酒摊之间转了好几圈,每个摊子都尝了三四回。摊主们渐渐看出了端倪,络腮胡脸沉了下来:“你这轻汉子,光尝不买,是来蹭酒喝的吧?” 老五嘿嘿一笑,装傻充愣:“哪能啊,我这不是还没挑好嘛。再尝最后一口,最后一口就决定。” 说着就伸手去拿酒碗。络腮胡一把按住他的手:“别尝了,再尝我就不客气了!”
老五见实在蹭不到了,也不恼,晃了晃已经有些发沉的脑袋,转身就往家走。一路上,冷风一吹,酒劲上来了,他脚步踉跄,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。路过的人见了,都摇摇头:“这老五,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,还有心思蹭酒喝,真是没救了。”
老五可不管别人怎么说,他只觉得肚子里暖烘烘的,浑身轻飘飘的,所有的饥饿和寒冷都被酒精驱散了。回到家,老五女人见他醉醺醺的样子,气不打一处来:“你又去蹭酒喝了?家里孩子都饿哭了,你还有心思喝酒!”老五摆了摆手,含糊不清地说:“别吵,别吵,过年了,喝点酒热闹热闹。”说完,就一头栽倒在冰冷的炕上,打起了呼噜。
老五女人看着他醉死的样子,又看了看蜷缩在角落里、眼巴巴望着她的孩子,忍不住抹起了眼泪。窗外的风还在呼啸,腊月的寒意在破旧的屋子里肆意蔓延,只有老五的呼噜声和偶尔的梦呓,诉说着他短暂的、虚幻的温暖。
时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,老五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,他们搬家到了云河镇的下街安家。
这个时期,后山的酿酒散户,将自家酿的杆杆酒在云河镇走街串巷去售卖。雨过天晴,远远的下街那条青石板路上只见一个年轻小伙子挑着两壶塑料桶,一边走一边吆喝“正宗青石崖的杆杆酒,味道纯的很!”杆杆酒的香味硬是把老五从屋里面“引到”屋门口,老五靠在自家掉了漆的门板上,他敞开那破旧的对禁衣裳、拖着一双被年代磨掉后跟的黑布鞋,堂屋大桌子放着一个绿色洋瓷碗,里面盛着满满的韭菜青辣子,旁边放着一个有豁豁破旧不堪的酒盅子。
老五嘴里叼着烟袋锅锅,把卖酒的小伙子喊住。
小伙子挑着塑料桶上了他的门上,只见小伙子用小小的黄色搪瓷缸缸倒出来一点递给老五。
老五将烟袋锅锅斜插在腰间的腰带上,接过黄色搪瓷缸,开始尝酒了。美美咂了一大口说:“哎!没尝到啥味道呀!”
小伙子无奈的撇了他一眼,又从塑料桶里面“嗻”了一黄色搪瓷缸,“叔,这次慢慢品哦,我爹今年酿的酒杆杆酒纯正很哦!”
老五开心地露出满嘴被烟草熏黄的牙齿,赶忙接过黄色搪瓷缸喂到嘴里,一缸缸酒瞬间下肚,他用袖子口抹去嘴角胡须上的酒滴,对小伙子说到“味道有点淡啊!还是不过瘾。”
小伙子应付地笑了说:“今天,我从中街到下街卖了50斤,街坊叔伯都夸我爹这酒酿的纯正、入口清香,还不上头。叔,你要不要买点?”
老五摆了摆手,算了吧,下次吧。
小伙子斜了斜眼睛,低头收拾好黄色搪瓷缸、塑料桶,小声说着:“酒都尝了3两了,回回到你门上都尝酒,就是不买酒。今后绕道走,不敢再让你看见了”。
老五假装没听到,从腰间取出烟袋锅锅,咳嗽一声转身进屋了...
时光荏苒,转眼老五早已离世多年,而老五尝酒的故事却在云河镇下街流传至今。
(作者:肖海娟)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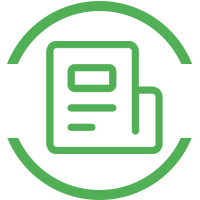
 微信号
微信号


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
 公网安备61019002002326
公网安备61019002002326